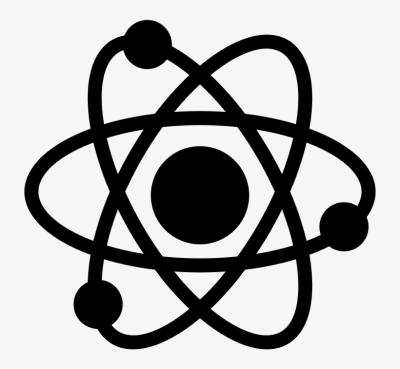对许多人来说,“衣柜永远少一件衣服”是再日常不过的烦恼;但对印度北部帕尼帕特(Panipat)纺纺织品回收厂工作的人来说,不只永远不缺衣服,每天面对的更是源源不绝、世界各地涌入的废弃衣物。
工人长期吸入超细纤维(microfiber)与粉尘,呼吸道疾病成为看不见的代价。而有毒废水则渗入土地与河川,使整座城市在“循环经济”的名义下逐渐窒息。
回收旧衣,最后去到哪里?欧洲“旧衣回收箱”象征善意循环,人们相信,捐出衣服能帮助有需要的人。“大家都以为,这些衣服会再利用”,格罗宁根大学(University of Groningen)研究员玛丽亚皮拉尔乌里韦(Maria Pilar Uribe)指出,“但现实是,大部分衣服最后都是丢掉,“进口”至另一个国家”。
一件不要的T恤,可能在欧洲某座大城市装箱,跨越多国来到全球二手衣服供应链的末端──印度有“世界旧衣之都”之称的帕尼帕特。每年约百吨废弃纺纺织品会来到这里,超过30万名工人每天在堆积如山的旧衣山上工作。
先进口,再出口《卫报》报道,进口至印度的旧衣会先分为两类:还可以穿的衣物(wearable clothing),直接送去二手市场,残损衣物(mutilated clothing)则撕碎、重新纺成新纱线。从夹克、裙子、开襟羊毛衫再到贝雷帽,这些废弃衣服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,无论高级品牌还是快时尚单品,原本丢到垃圾掩埋场的衣物可拥有新生命。
首先,工人会将衣服一件件撕开,拆除拉链、钮扣和标签。接着依颜色分类:红色、蓝色、绿色和大量的黑色。机器将这些布料撕成更小碎布,另一台机器再把羊毛、丝绸、棉花与聚酯等纤维混合,重新纺成纱线。经过漂白、染色与编织后,制成新毛毯、地毯、抹布等家居用品,再出口至世界各地。
一切看似环保再利用的循环,却有不少负面影响。负责监测纺织废料的Reverse Resources的项目经理伊娜巴尔古纳(Ina Bharguna) 表示:“所有等级的材料──从聚酯运动裤到棉质衬衫──都一起撕碎成所谓“劣质纱线”(shoddy yarn),”
印度工人的日常:剪开旧衣,吸入灰尘这些重现的劣质纱线,里面不可能没有微塑胶成分。
27岁的妮尔玛黛维(Neerma Devi)工作就是剪开旧衣物、撕裂袖口,再将碎片送进轰轰作响的机器。她每剪一刀,房间就会扬起另一团棉絮与粉尘,尽管黛维用头巾紧紧绕在脸上,仍无法阻止粉尘吸入肺中。
六年前,黛维与丈夫来到帕尼帕特,期盼能在这里找到稳定的工作。如今,她每周工作六天,却也因此患严重的职业伤害,每天去医院报到已成为家常便饭,“医生告诉我是因我每天吸入这些灰尘。他给我药,但只有服药期间才有效。一旦停药,咳嗽就会复发。他说我应该辞掉这份工作。但我负担不起。”
讽刺的是,这样令人“窒息”的工作环境,成为现在支撑全球贸易的重要一环。

加纳旧法达玛(Old Fadama)的纺纺织品垃圾场,也是全球最大垃圾掩埋场之一。(Source:达志形象)
每口呼吸,换来无法治愈的疾病《美国呼吸和重症监护医学期刊》(ATS Jourmals)研究显示,长期暴露超细纤维环境,尤其尼龙,会损害气道上皮细胞修复与生长,对肺组织造成严重影响与损害。雪梨科技大学(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)研究发现,这些微塑胶深入呼吸道,更可能导致哮喘、器官纤维化及慢性阻塞性肺病(COPD)等。
黛维的公公在衣物回收厂工作多年,如今因患COPD导致肺部损伤严重,就连吞咽都会引发剧烈咳嗽与疼痛,甚至呼吸困难。医生告诉他COPD无法治愈,只能尽力减缓恶化。
黛维丈夫凯拉什库马尔(Kailash Kumar)也在同工厂工作,“没有口罩、没有面罩,整个工厂就像一个密闭空间,几乎没有通风。”库马尔说道。他很清楚自己每天吸进去的是什么,医生警告他,常年吸入这种空气,可能会让他步上父亲后尘,但现实让他没有退路。
老板:不就只是灰尘和绒毛哈里亚纳邦劳工部高级官员拉梅什乔德哈里(Ramesh Chawdhary)也承认许多任务厂条件非常恶劣。“工作环境令人难以忍受,我们经常遇到呼吸问题、偏头痛、皮肤感染,甚至是癌症等病例。长期暴露这种环境,后果十分严重。”
他补充,虽然部分工厂仍提供基本的防护措施,但与实际风险相比,几乎微不足道。“大多数业主并不优先考虑工人安全,漂白与染色部门尤其危险。工人往往得徒手接触硫酸等有毒化学品。”
然而,黛维的老板完全无动于衷。“我们不使用任何化学物质。只有灰尘和绒毛,怎么会造成什么严重问题?一点点咳嗽和感冒经常见。”他说。虽然工厂有提供口罩,但多数工人不愿意戴,反而抱怨戴口罩太闷、感觉窒息。
当地河水也生病了这些旧衣回收工厂不仅让工人生病,也让整座城市染上一层有毒物质。帕尼帕特有超过400家注册的染色与漂白厂,以及至少200家非法工厂。环保部门估计,约80%未经处理、含重金属与化学染剂的废水会直接进入工业水道,最后流入亚穆纳河(Yamuna River),成为德里(Delhi)下游的污染来源。
4月哈里亚纳邦污染控制委员会的实验室发现,排水沟的溶解固体含量几乎是规定上限四倍,水氧量不到标准一半,导致鱼虾等生物几乎无法生存。《卫报》报道,有些工厂会随便地上挖坑,让有毒废水直接渗入地底。
喝水变成诅咒,重金属污染蔓延全村住在帕尼帕特附近的哈特杰辛格(Hartej Singh),发现地下水无法饮用后,决定封闭自家钻井,“这里的水已成为我们最大诅咒,这条排水渠附近每口井,带来的只有痛苦与疾病。”当地村民表示,皮肤病几乎遍及全村,有些人甚至患癌症。居民认为,这与污染的水有关。
2022年印度水资源、河流发展与恒河复兴部(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)报告指出,帕尼帕特附近地下水已被锰、铅、硝酸盐和氟污染,部分地区还检出镉、镍、锌、铜等重金属。
同年,《欧洲经济快报》(European Economics Letters)调查显示,过去五年间,帕尼帕特周边地区有近93%家庭出现严重健康问题,高血压、糖尿病与心血管并发症当地广泛流行,又以皮肤疾病更普遍,尤其需要经常接触衣物或取水的女性与儿童群体。

亚穆纳河流经的马图拉(Mathura)。(Source:pexels)
环保禁令难落实、罚款形同虚设《卫报》报道,今年印度国家绿色法庭(National Green Tribunal)下令关闭31家非法漂白与染色工厂,但环保人士瓦伦古拉蒂(Varun Gulati)直言,效果非常有限,“过去五年,约150家非法漂白工厂关闭,但执法力度不一,加上官员人手不足,工厂换个名字就能重新开业。”
古拉蒂指出,罚款制度同样形同虚设。污染控制委员会共开出约50亿卢比罚单,但实际仅追回七成。“即便开了罚单,也会减免或未收取,甚至根本不执行。”古拉提说。
总理力挺可持续发展回收,但工人健康呢?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(Narendra Modi)3月广播节目谈及“快时尚”产生的纺织废料对环境造成的冲击。他指出,“全球只有不到1%纺织废料回收再制成新衣”,并强调印度为全球第三大纺织废料产生国,亟需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。
莫迪总理同时赞扬印度在“可持续发展纺织废料管理”的努力与成果。他表示,帕尼帕特成为全球纺纺织品回收的中心;班加罗尔(Bangalore)以创新技术处理纺织废料问题;蒂鲁普尔(Tiruppur)则以废水处理与再生能源计划,废料管理取得显著进展。
然而,全球旧衣循环链,这座“全球纺纺织品回收中心”以另一种形式掩盖环境与劳动剥削的现实。
帕尼帕特纺纺织品回收厂Shankar Woollen Mills经营者阿什维尼库马尔(Ashwini Kumar)表示,“我们做的是有价值的工作,想想这些布料如果丢弃,会造成多大的浪费。”
但对仍在工厂上班的黛维而言,她吸的每口空气,都是必须承受的代价。“想到有天我可能会变成像公公那样久病缠身,我非常害怕。但目前,这是我们唯一的生存方式。”
(首图为帕尼帕特纺织厂的染布工人,来源:达志形象)